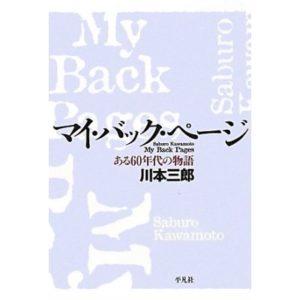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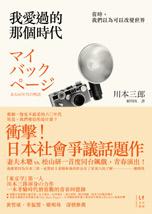
书名:マイ・バック・ページ(My back pages )-ある60年代の物語
台版译名:我爱过的那个时代——当时,我们以为可以改变世界(译者: 赖明珠)
作者:川本三郎
出版社: 平凡社; 復刊版 (2010/11/26)
ISBN-13: 978-4582834840
【作者介绍】
川本三郎/KAWAMOTO SABURO 1944~
评论家。1944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朝日新闻社。历经《周刊朝日》、《朝日杂志》记者,进入评论活动。自由文字工作者,持续从事文艺、电影评论、翻译、随笔等多项领域分明的执笔活动。特别喜欢楚门‧卡波提作品,并翻译其作品无数。
著作《大正幻影》(获Suntory学艺赏)、《荷风与东京》(获读卖文学赏)、《林芙美子的昭和》(获每日出版文化赏、桑原武夫学艺赏)、《看电影就知道的事1~3》、《现在,还想妳》等多数。
【内容介绍】
Suntory学艺赏×读卖文学赏× 桑原武夫学艺赏 × 每日出版文化赏受赏作家
如果不抱幻象去爱,就是所谓的爱,我可以说爱过那个世代……
一九六八年,日本各大学发起了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浪潮,出现学生组织的「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罢课、占领大学校园等场面愈演愈烈。一如许多目前仍活耀于日本艺文界的创作者,作者川本三郎与他们同样是「全共斗世代」。
在这个日本社会思潮震荡最剧烈的时期,川本三郎以一个初出茅庐刚跑周刊新闻的新人记者身分,完整描绘出当时社会浪潮,让这本作品成了六○年代的最真实见证。而他更亲眼目睹东大「安田讲堂事件」,这个大时代发生的事件,后来履次由村上春树关键性地写在《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挪威的森林》、《1Q84》等作品中。
时间也无法疗愈的伤痛,一段作者数度提笔无法写成的青春挫折物语。
本书文章最早连载于一九八六年至八七年日本文化创意人喜爱的艺文杂志《SWITCH》,专栏名称为「The Reading」,由该志发行人新井敏记先生总策划,并与角取明子小姐亲自拜会川本三郎邀稿。最初原本只是希望让八○年代的年轻读者能理解六○年代的人事物而书写,没想到川本三郎写着写着,最后却变得不得不整理思绪,提到一九七二年改变他一生,让他久久无法提笔写作的专访思想犯(杀人犯)事件。
他因为私下采访嫌犯并湮灭证据,走在「记者道德」与「公民道德」的法律边缘。最后还是因为受不了精神压力,遂向警方坦承事件发生经过而身系囹圄。因为这桩「朝霞自卫官杀害事件」,他成了日本最受争议的文坛评论家。正因为如此大胆的交涉过程,更清楚地描绘出当时年轻人的不安与冲动。尽管伤痛,作者藉由这些文字的呈现,宛如电影一般让我们清楚看到了日本六○年代末期,一个个「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做到」的青春姿态。
目录:
Side-A
◎看了《没有阳光》那天
时代一点都不温柔,那个时代的象征,说起来就是经常在下雨……
◎69年夏
回想起,那太阳非常热的六九年盛夏。我二十五岁。
◎蒙受幸福恩惠的女子,死了
我想她一定是个比别人加倍温柔的女孩,但似乎不喜欢当一个艺人,做演员这个工作。
◎死者们
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人死掉,生的中心就有死,而且「我们」并不避开那死,反而想去亲近。
◎罪恶感
记者难道不是应该先去救助即将被杀害的人吗?在按下快门之前,不是应该先制止美军吗?
◎拒绝采访
我想这些孩子拥有可以反抗的父亲或许是幸福的。
◎都会有时很美丽
我离大学愈来愈远,生活绕着电影、爵士乐、和戏剧打转,街头成了「我的大学」。
◎远离越南
那说明了不管怎么反对越南战争,自己反正不是当事者,只是从安全地带鼓动反动运动而已……
◎现代歌情
摇滚,是在越南战争的体验中所产生并茁壮起来的美国年轻世代的音乐。生活在温吞吞日常中的我们,是不会懂得摇滚优点的……
Side-B
◎逮捕之前I
宫泽贤治和清水乐团-这两点让我信任了K……
◎逮捕之前II
我这边冒着自己的风险还坚守「记者的道德」这原则,不向警察「通报」K的事。
◎逮捕和解雇
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我被埼玉县警察逮捕,因「湮灭证据」的嫌疑。
◎后记
◎新装版出版记〈三个时间〉
书摘:
(1)
我离大学愈来愈远,生活绕着电影、爵士乐、和戏剧打转,街头成了「我的大学」。母亲担心地说:「你到底打算怎么办?有没有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我并没有勇敢到回嘴「啰嗦」的地步,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地继续在街头流浪。像中了毒瘾般,对街上的嘈杂也会上瘾。一到华灯初上的时分,就会开始迷恋起嘈杂的街头,一留神时,人已经身在新宿街上逛了。
有一次,我曾经对「现代诗」的山内先生提到:「我也想当吃茶店老板。」平常很和气的山内先生,只有那次很生气地说:「煮一杯咖啡,以你那样的玩票态度都不行噢。」
越战打得愈来愈激烈。日本媒体果敢地开始展开反战活动。尤其是自由摄影记者陆续去到越南,发表在战场拍回来的活生生血淋淋战场相片。我看到这样的工作,想做记者工作的心就变得更坚定。
因此大学四年级夏天就去报考朝日新闻社,却在面试时落榜。也不敢保证第二年如果重考是否能考上,事到如今也不能去银行或商社应征了。
没有被公司录用的人,无论是谁都会感到不安和孤立,以我的情况,又处于「就职浪人」这种特殊状况,更认定自己是孤独一人了。
虽然政治意识很强,但几乎和政治运动无缘。对所谓人际关系这东西极力避免密切牵扯的「胆小个人主义者」来说,政治运动犹如穿着脏鞋子不客气地一脚踏进人家屋里,侵犯私生活等缺乏细腻感觉的强者行为。
虽然如此,我依然决定当一个就职浪人,这是深受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发生的所谓「第一次羽田事件」冲击。当时的佐藤首相,冒着国内重度批判越南战争的声浪,毅然访问越南,对这点,反代代木系全学连的学生高喊「阻止佐藤出访」口号,在羽田机场附近展开示威游行,在和警察队伍冲突之中,和我同世代的京都大学生死掉了。
这个事件带给学生们很大的冲击。「他死掉了,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对这样的质问,谁都苦恼烦心,也就是所谓「10.8冲击」。对于被称为全共斗世代的那世代人来说,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成为难以忘记的「纪念日」。就像美国六○年代「肯尼迪总统被杀时,你在做什么?」这句话被当成世代的共通语言般,对六○年代的日本来说,「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京大生山崎博昭死去时,你在做什么?」也成为共通的沉重问题。
确实对我(们)来说,那个时代并“不是我时代”。有死,有无数的败北。但那个时代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时代”。不是自我中心主义(me-ism),而是我们主义(we-ism)的时代,任何人都试着为别人设想。把越南被杀的孩子们想成自己的事,对战争试着表达抗议的意志,试图否定被编入体制内的自己。我只想把这件事珍惜地留在记忆中。
(2)
自由摄影师中平卓马在某报纸上所写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记录在当时的日记里头。 “现在的日本高喊反对战争,丝毫不需要有个人的决心。总之西班牙很远,而越南更远”“所谓打倒资本主义推动世界革命!……支持这些口号的语言,缺乏真实感。” 今天,回想当年时,往往会说“六十年代还有正义”,这样美化地说,肯定是错了。我们确实可能是打内心深处反对越战的。但同时,我们对一边身在安全地带一边反对战争的这种“正义”也感到厌恶和愧疚。因此愈谈到“正义”,反而愈想保持“沉默”。“正义”和“沉默”几乎只隔着一层纸。OWL的M和H,愈跟美军交往愈倾向于保持“沉默”,变得没办法放怀去从事反战运动,我想是因为这样。
(3)
六九年一月十八日早晨。我无法面对安田讲堂超过一小时。当眼前和自己拥有同样想法的人,正把自我怀疑推向极限时,反观自己却在安全地带“旁观”让我很痛 苦。我对一个前辈记者说:“我想回去了。”他回应:“你要回去没关系,不过因为痛苦就不再看的话,是当不成记者的哦。”这种专业意识让我很敬佩,不过,要 我留在现场还是受不了,于是离开了校园。我对于佩戴报导臂章走过机动队前安全的自己也感觉很厌恶。 守在安田讲堂里的学生们坚守了两天,第二天十九日傍晚,终于全体遭到逮捕。十九日下午五时四十分,进入安田讲堂的机动队把屋顶的红旗拆下。一切都结束了, 然后,一切都开始了。 “如果,我不保护自己的话,谁会保护我呢?但,如果我只想到自己的话,我又为什么存在呢。”
【同名电影改编】

昔日的我 マイ・バック・ページ (2011)
导演: 山下敦弘
主演: 妻夫木聪 / 松山研一 / 忽那汐里 / 中村苍 / 石桥杏奈 / 韩英惠 / 長塚圭史 / 山内圭哉
上映日期: 2011-05-28
获2011年电影旬报十佳第九名。